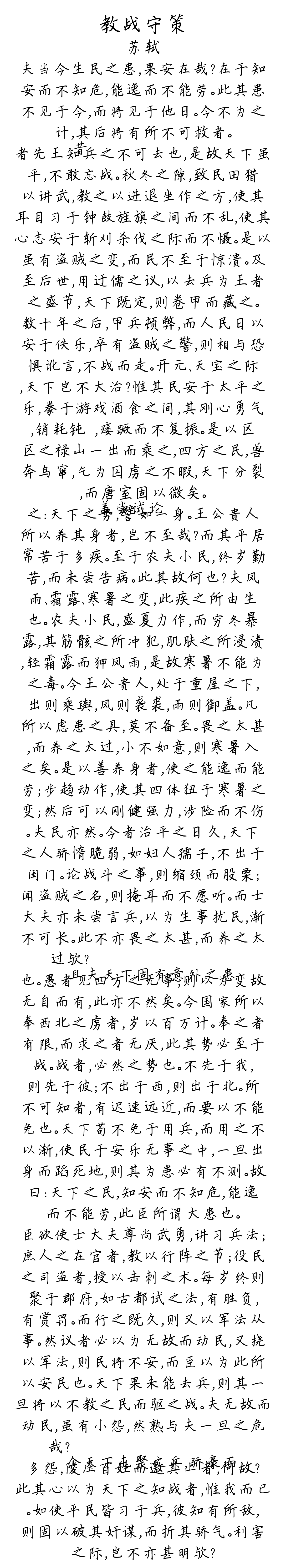教战守策
夫当今生民之患,果安在哉?在于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。此其患不见于今,而将见于他日。今不为之计,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。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,是故天下虽平,不敢忘战。秋冬之隙,致民田猎以讲武,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,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,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。是以虽有盗贼之变,而民不至于惊溃。及至后世,用迂儒之议,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,天下既定,则卷甲而藏之。数十年之后,甲兵顿弊,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,卒有盗贼之警,则相与恐惧讹言,不战而走。开元、天宝之际,天下岂不大治?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,豢于游戏酒食之间,其刚心勇气,销耗钝眊,痿蹶而不复振。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,四方之民,兽奔鸟窜,乞为囚虏之不暇,天下分裂,而唐室固以微矣。 盖尝试论之:天下之势,譬如一身。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,岂不至哉?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。至于农夫小民,终岁勤苦,而未尝告病。此其故何也?夫风雨、霜露、寒暑之变,此疾之所由生也。农夫小民,盛夏力作,而穷冬暴露,其筋骸之所冲犯,肌肤之所浸渍,轻霜露而狎风雨,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。今王公贵人,处于重屋之下,出则乘舆,风则袭裘,雨则御盖。凡所以虑患之具,莫不备至。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,小不如意,则寒暑入之矣。是以善养身者,使之能逸而能劳;步趋动作,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;然后可以刚健强力,涉险而不伤。夫民亦然。今者治平之日久,天下之人骄惰脆弱,如妇人孺子,不出于闺门。论战斗之事,则缩颈而股栗;闻盗贼之名,则掩耳而不愿听。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,以为生事扰民,渐不可长。此不亦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欤?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。愚者见四方之无事,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,此亦不然矣。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,岁以百万计。奉之者有限,而求之者无厌,此其势必至于战。战者,必然之势也。不先于我,则先于彼;不出于西,则出于北。所不可知者,有迟速远近,而要以不能免也。天下苟不免于用兵,而用之不以渐,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,一旦出身而蹈死地,则其为患必有不测。故曰:天下之民,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,此臣所谓大患也。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,讲习兵法;庶人之在官者,教以行阵之节;役民之司盗者,授以击刺之术。每岁终则聚于郡府,如古都试之法,有胜负,有赏罚。而行之既久,则又以军法从事。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,又挠以军法,则民将不安,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。天下果未能去兵,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。夫无故而动民,虽有小怨,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? 今天下屯聚之兵,骄豪而多怨,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,何故?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,惟我而已。如使平民皆习于兵,彼知有所敌,则固以破其奸谋,而折其骄气。利害之际,岂不亦甚明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