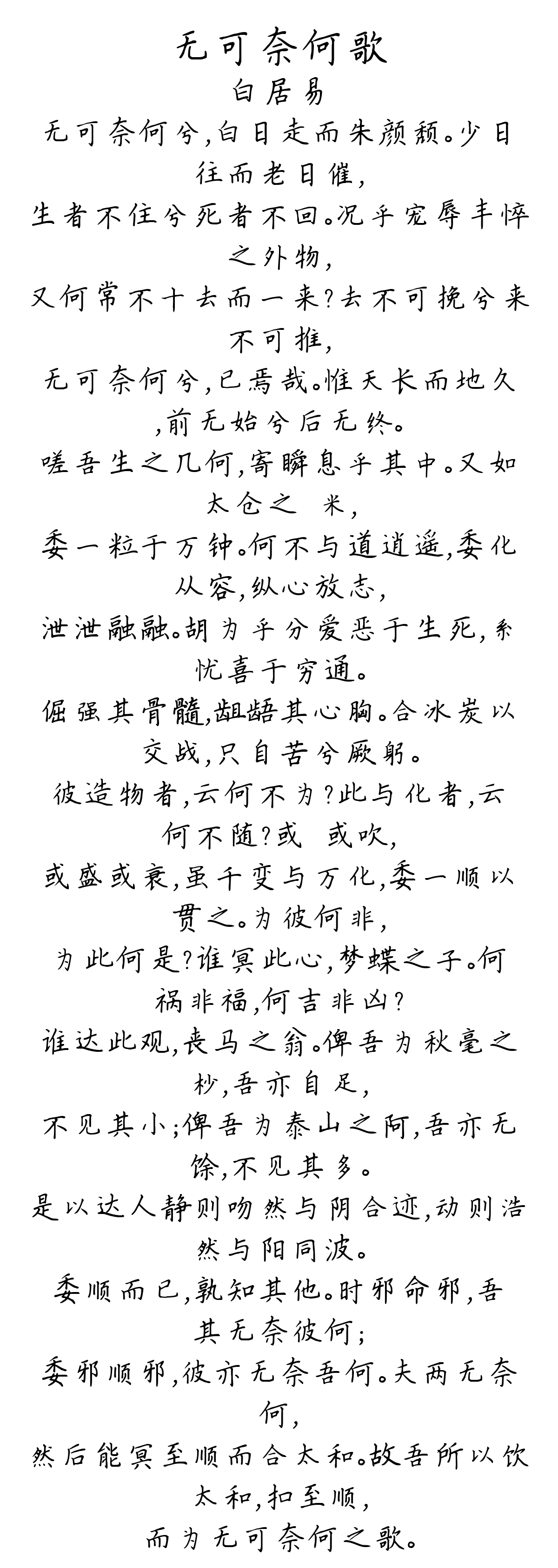无可奈何歌
无可奈何兮,白日走而朱颜颓。少日往而老日催,
生者不住兮死者不回。况乎宠辱丰悴之外物,
又何常不十去而一来?去不可挽兮来不可推,
无可奈何兮,已焉哉。惟天长而地久,前无始兮后无终。
嗟吾生之几何,寄瞬息乎其中。又如太仓之稊米,
委一粒于万钟。何不与道逍遥,委化从容,纵心放志,
泄泄融融。胡为乎分爱恶于生死,系忧喜于穷通。
倔强其骨髓,龃龉其心胸。合冰炭以交战,只自苦兮厥躬。
彼造物者,云何不为?此与化者,云何不随?或喣或吹,
或盛或衰,虽千变与万化,委一顺以贯之。为彼何非,
为此何是?谁冥此心,梦蝶之子。何祸非福,何吉非凶?
谁达此观,丧马之翁。俾吾为秋毫之杪,吾亦自足,
不见其小;俾吾为泰山之阿,吾亦无馀,不见其多。
是以达人静则吻然与阴合迹,动则浩然与阳同波。
委顺而已,孰知其他。时邪命邪,吾其无奈彼何;
委邪顺邪,彼亦无奈吾何。夫两无奈何,
然后能冥至顺而合太和。故吾所以饮太和,扣至顺,
而为无可奈何之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