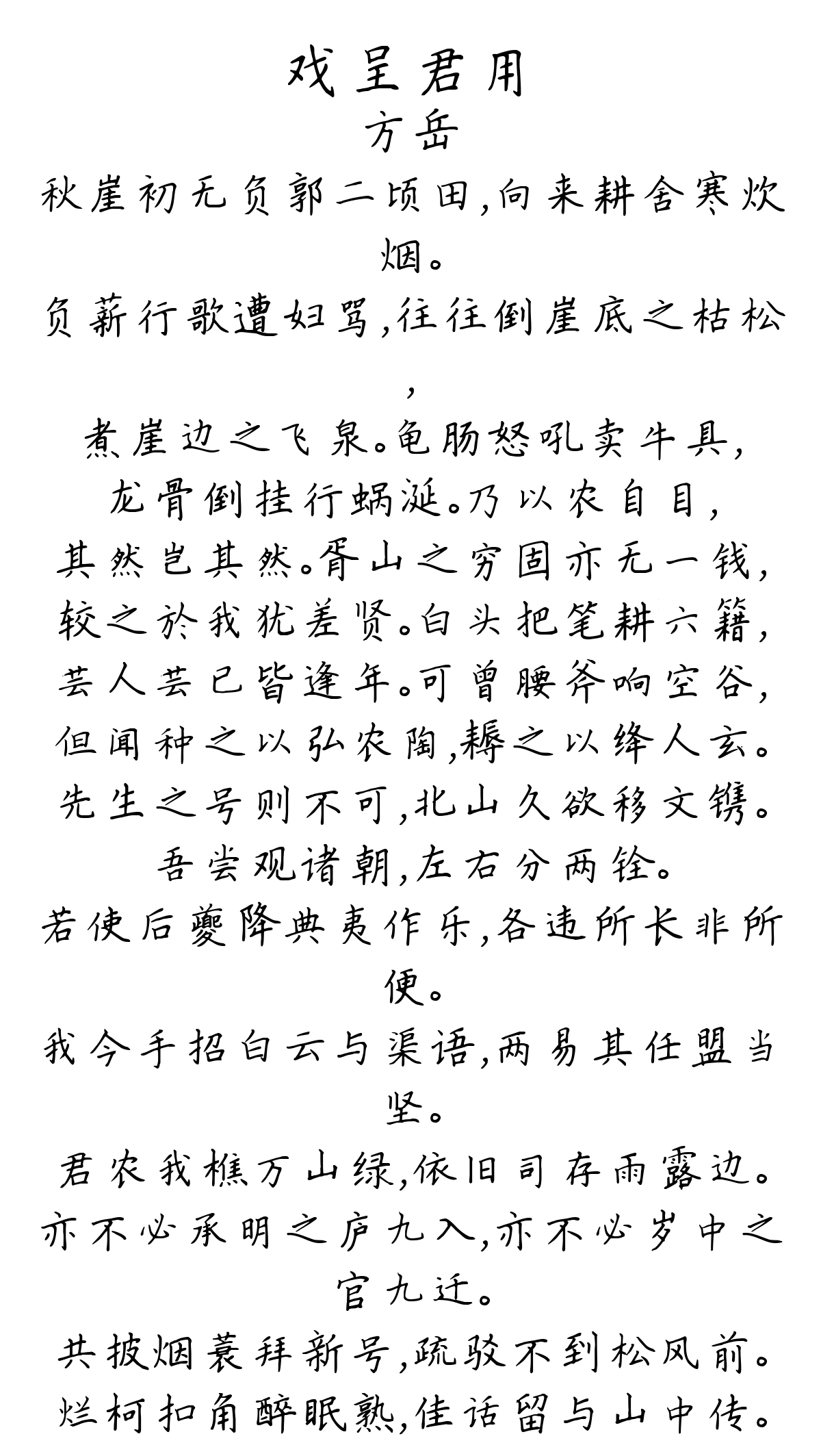戏呈君用
秋崖初无负郭二顷田,向来耕舍寒炊烟。
负薪行歌遭妇骂,往往倒崖底之枯松,
煮崖边之飞泉。龟肠怒吼卖牛具,
龙骨倒挂行蜗涎。乃以农自目,
其然岂其然。胥山之穷固亦无一钱,
较之於我犹差贤。白头把笔耕六籍,
芸人芸已皆逢年。可曾腰斧响空谷,
但闻种之以弘农陶,耨之以绛人玄。
先生之号则不可,北山久欲移文镌。
吾尝观诸朝,左右分两铨。
若使后夔降典夷作乐,各违所长非所便。
我今手招白云与渠语,两易其任盟当坚。
君农我樵万山绿,依旧司存雨露边。
亦不必承明之庐九入,亦不必岁中之官九迁。
共披烟蓑拜新号,疏驳不到松风前。
烂柯扣角醉眠熟,佳话留与山中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