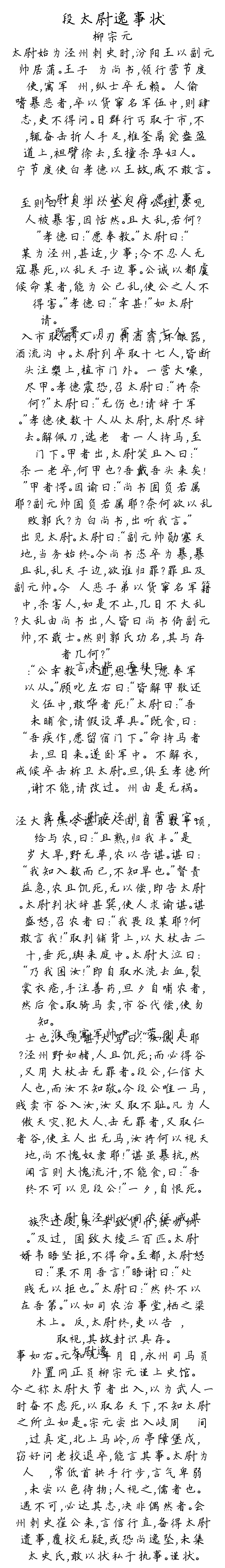段太尉逸事状
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,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。王子晞为尚书,领行营节度使,寓军邠州,纵士卒无赖。邠人偷嗜暴恶者,卒以货窜名军伍中,则肆志,吏不得问。日群行丐取于市,不嗛,辄奋击折人手足,椎釜鬲瓮盎盈道上,袒臂徐去,至撞杀孕妇人。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,戚不敢言。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,愿计事。至则曰:“天子以生人付公理,公见人被暴害,因恬然。且大乱,若何?”孝德曰:“愿奉教。”太尉曰:“某为泾州,甚适,少事;今不忍人无寇暴死,以乱天子边事。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,能为公已乱,使公之人不得害。”孝德曰:“幸甚!”如太尉请。 既署一月,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,又以刃刺酒翁,坏酿器,酒流沟中。太尉列卒取十七人,皆断头注槊上,植市门外。晞一营大噪,尽甲。孝德震恐,召太尉曰:“将奈何?”太尉曰:“无伤也!请辞于军。”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,太尉尽辞去。解佩刀,选老躄者一人持马,至晞门下。甲者出,太尉笑且入曰:“杀一老卒,何甲也?吾戴吾头来矣!”甲者愕。因谕曰:“尚书固负若属耶?副元帅固负若属耶?奈何欲以乱败郭氏?为白尚书,出听我言。”晞出见太尉。太尉曰:“副元帅勋塞天地,当务始终。今尚书恣卒为暴,暴且乱,乱天子边,欲谁归罪?罪且及副元帅。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,杀害人,如是不止,几日不大乱?大乱由尚书出,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,不戢士。然则郭氏功名,其与存者几何?” 言未毕,晞再拜曰:“公幸教晞以道,恩甚大,愿奉军以从。”顾叱左右曰:“皆解甲散还火伍中,敢哗者死!”太尉曰:“吾未晡食,请假设草具。”既食,曰:“吾疾作,愿留宿门下。”命持马者去,旦日来。遂卧军中。晞不解衣,戒候卒击柝卫太尉。旦,俱至孝德所,谢不能,请改过。邠州由是无祸。 先是,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。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,自占数十顷,给与农,曰:“且熟,归我半。”是岁大旱,野无草,农以告谌。谌曰:“我知入数而已,不知旱也。”督责益急,农且饥死,无以偿,即告太尉。太尉判状辞甚巽,使人求谕谌。谌盛怒,召农者曰:“我畏段某耶?何敢言我!”取判铺背上,以大杖击二十,垂死,舆来庭中。太尉大泣曰:“乃我困汝!”即自取水洗去血,裂裳衣疮,手注善药,旦夕自哺农者,然后食。取骑马卖,市谷代偿,使勿知。 淮西寓军帅尹少荣,刚直士也。入见谌,大骂曰:“汝诚人耶?泾州野如赭,人且饥死;而必得谷,又用大杖击无罪者。段公,仁信大人也,而汝不知敬。今段公唯一马,贱卖市谷入汝,汝又取不耻。凡为人傲天灾、犯大人、击无罪者,又取仁者谷,使主人出无马,汝将何以视天地,尚不愧奴隶耶!”谌虽暴抗,然闻言则大愧流汗,不能食,曰:“吾终不可以见段公!”一夕,自恨死。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,戒其族:“过岐,朱泚幸致货币,慎勿纳。”及过,泚固致大绫三百匹。太尉婿韦晤坚拒,不得命。至都,太尉怒曰:“果不用吾言!”晤谢曰:“处贱无以拒也。”太尉曰:“然终不以在吾第。”以如司农治事堂,栖之梁木上。泚反,太尉终,吏以告泚,泚取视,其故封识具存。 太尉逸事如右。元和九年月日,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。 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,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,以取名天下,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。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,过真定,北上马岭,历亭障堡戍,窃好问老校退卒,能言其事。太尉为人姁姁,常低首拱手行步,言气卑弱,未尝以色待物;人视之,儒者也。遇不可,必达其志,决非偶然者。会州刺史崔公来,言信行直,备得太尉遗事,覆校无疑,或恐尚逸坠,未集太史氏,敢以状私于执事。谨状。